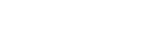第154期 臺灣社區發展50年—回顧與前瞻(2016年06月)
從「社區發展」到「社會企業」?關於社會企業的政策議程和政治想像
在從事社區理論和社區工作實務的研究中,這幾年最常聽到的是許多夥伴們高喊用社會企業做為社區發展或社區產業的補充甚或替代方案[1](Davies, 2012),來解決社區、政府、市場甚至是非營利組織都無力面對的社會問題及其後果的擴大。同樣是關心著第三部門或非營利組織研究的發展(張世雄,2001),也看到類似情形在醞釀發展(官有垣,2007),更得到政府部門的轉型鼓勵,帶有著政策利多誘因和配套資源的支持。於是,那股現在「我們都是社會企業」的氣氛,到處飄散且快速盛行著。當然,這自然也引發了許多的質疑和懷疑:行政院所宣告的2014年為「社企元年」,「到底是誰的社會企業元年?」,甚或是「誰才是社會企業?」的認同與排除問題。更值得深思的不只是新瓶裝舊酒否,而是會不會又是另一個「好主意變成壞點子」[2],或成為「橘越淮為枳」[3]的舶來品呢?
在許多時候,英國被視為是社會企業法制和社會投資市場發展最完備的國家(楊衡,2014;劉子琦,2015),特別是自2010年保守黨和自民黨聯合執政開始推動的「大社會」(Big Society)政治願景(張世雄,2013),有著「大社會資本」(Big Society Capital, 2012)和「大樂透基金」Big Lottery Fund(2011)的獨立設置[4],作為媒介社會投資和創業需求間制度管道(盧俊偉,2014)。但這其實也真的不新。除了是延續著前朝新工黨政府的「第三條路」路線(Third Way)(Giddens, 1999)及在第三部門(Third Sector)框架中的發展,卻意圖扭轉原先為「青年政策」的設定目標,給予更多的資本化、市場化和商業化政策(推力)誘因的「社會企業」政策議程外,更因為他們都還是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的真正繼承人:所謂的「柴契爾的兒子們」(Jenkins, 2006)。這讓我們有必要認清政策議程和(關於理想社會)政治想像或願景之間的特定連結,以及他們和金融化資本主義經濟的動態互動歷史發展(Teasdale, 2011)。我們或許可以先暫時簡化地說:柴契爾政府面對著英國的福利國家,首先給予(包括1979年競選承諾和1980年勝選立法出售社會住宅給原有承租戶[5]和1981年開始首波出售五大國有企業[6])「私有化」(Privatization)和(1990年NHS全民健康服務的購買者與提供者分離)「內部市場化」;新工黨執政則接受其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的政府思維,發展第三部門和公民社會來做為「夥伴」和公共服務「契約外包」的提供者;而卡麥隆的聯合政府則是還要把第三部門也給予企業化、商品化和市場化為真正會賺錢的「社會企業」(Frances and Cuskelly, 2008; Davies, 2012),以合理化財政「樽節政策」(Austerity)大幅進行刪減社會與公共服務預算(張世雄,2013)。
時序跨入二十一世紀,「社會企業」的概念和理論頓時成了一個建構論述及議題的政治戰場(Ridley-Duff, Bull and Seanor, 2008; Ridley-Duff and Bull, 2011)。一方面,概念的衍生界定向外擴張性的與日劇增;隨著新名詞「社會商業」(Social Business)、「公益公司」(Benefits Corporation)(Honeyman, 2015)、或「B型公司」(B-Cop)的新增加入[7],以及美國數州通過州法建立和保護(可以不受股東操弄)的「低獲利責任有限公司」(Low-Profit, Limited-Liability Company, L3C),而營利和非營利之間的光譜辨識,也愈來愈趨複雜和不易分辨(Jones, 2015; Rifkin, 2014)。另方面,「社會企業」理論也開始有了關於實質內涵的論證與辨析,以區辨誰才是真的,或至少是更接近社會企業的目的或價值。有人極力要區辨創業精神(Enterpreurship)和企業(Enterprise)之間的重要差別(Grassl, 2012);也有指出社會問題解決和社會影響(social impact)關注之間的顯著不同。特別是把焦點集中在卡麥隆政府所謂的「把社會帶回來」,刻意操作和翻轉柴契爾「只有個人,沒有社會這事物存在」的冷酷個人主義形象,作為對抗新工黨「大政府」的策略,實際上卻只不過是種「言詞巧弄、虛構的社會」(Levitas, 2012; Corbett and Walker, 2013)。這些分析和提議,都指向一個沒有單一標準模式和非契約關係的市民社會組織,以及應該是鼓勵多元主義組織模式的創新和創業精神。
如果排除了捨本(創新)逐末(企業組織)的追求,這當然就包括了不一定要先有賺取實質現金收入或取得足夠資本存量,或得要先僱有足夠(但未必是非低薪雇用)人力,甚至要有財稅優惠或優先承攬公共工程暨服務的條件,才能夠去從事解決社會問題的「創新」工作,貢獻於增進國家GDP成長率的經濟效率誘因。這不可避免地就涉及到「社會企業」的目標設定:至多只會是金融化資本主義的人道化粧師(被企業化的慈善組織和被賦予社會責任的企業公司),一種「文明化資本主義」(Civilizing Capitalism)的修正;或者是要以公民生活增進為目標,取代經濟成長率優先,推動「去柴契爾主義化」第三條路的「公民的資本主義」(Civic Capitalism)(Hay and Payne, 2015),還是可以真正激進推動社會經濟結構改變的新政治力量,朝向非資本主義另類典範「協同共享」(Collaborative Commons)的「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Rifkin, 2014),或作為參與民主政治基石的「公民經濟」(Civic Economy)新體制。再回過頭來反說,這種非金融信用化和非市場獲利優先的經濟組織,方能挑戰任何政府試圖打造社會企業部門作為「第四部門」的政策議題,甚至將自己定位成一個「社會企業型政府」的國家政治改造議程(盧俊偉,2014)[8]。在釐清這「社會」導引協作共享的認識行動,開發鑲崁在當代物聯網經濟技術條件中的創新和創業潛能(Rifkin, 2014),那麼從「社區發展」到「第三部門」、「社會企業」的半個世紀[9]社會發展旅程,才能有結社式「社會」協作經濟共享的真實意義,作為實踐成熟「公民」的民主參與政治之平等、互賴和互信基礎(張世雄,2014)。
在邁向這想像未來的漫長旅程中,本文先提出我國社會企業倡導行動和政府政策回應的一般觀察,包括學步1980年代以來英國保守黨啟動的「對福利作戰」(War on Welfare)的系列改革。其次,分析英國福利國家危機改革歷程的柴契爾主義路徑依賴,以市場驅動(market-driven)的社會政策,建構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思維主導的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秩序,和不斷陷入反覆危機中的失序。「社會企業」作為回應政府和市場雙重失靈下,自願、非營利和第三部門尋求新的社會改變和資源,相對於來自企業對公司社會責任和永續生態環境的覺醒,試圖以創新行動和改變組織經營,讓資本主義的市場效率轉變成為服務社會價值和目標的工具,卻在概念上與理論上不斷徘徊在營利和非營利之間。在危機和契機之間,本文試圖從政治經濟體制的理念類型區分,提供進一步探討「社會企業」可能扮演的角色、組織型態和制度發展限制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