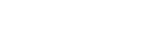第137期 取精用弘彰顯社會工作(2012年03月)
惡水上的大橋——跨越教育與社政的學校社會工作
1970 年,那是一個轉換和不確定的年代,在美國,學生因為越戰紛亂不已,那一年發生美國第一次全國學生總罷課(因為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1],那一年Simon &Garfunkel 用帶點哀柔的聲音唱出「Whenyou’re weary, feeling small,When tears are inyour eyes,I will dry them all,I’m on your side,when times get rough …」(當你感到疲累渺小,當眼淚在你眼中閃爍,我會為你拭去你的淚水,我就在你身旁,當世局艱難)[2],同一時期,美國學校社會工作透過教育的立法承認了學校社會工作的合法性,NASW 也發展第一套學校社工服務準則(蘇培茹,2009),美國學校社會工作進入了社區學校關係時期,不僅學校社會工作人數明顯增加,工作重點更強調家庭、社區、學校內的團隊合作關係(林萬億、王靜惠,2004),正如惡水上的大橋,學校社會工作跨越在學校與家庭、社區之間,也跨越在教育和社政中間,尋求積極有效的角色介入,協助許多困在「惡水」中的學生。
同一時期,我國學校社會工作進入倡議階段,1970 年,由教育部、內政部、經合會(經建會)、司法行政部(法務部)所通過的「中華民國兒童少年發展方案」中,明文規定應建立學校社會工作員的制度,以提升國民中小學的就學率與教學效果(林勝義,2003),但由於沒有教師資格的社會工作員仍無法進入校園,跨專業的思維立意甚佳,學校社會工作也僅是挹注學校輔導資源的定位。其後,學校社會工作進入民間單位試辦時期,由CCF 參照香港的學校社會工作方法與內容擬訂服務方案,卻也在實施將近八年之後(1977~1985),因為民間機構介入學校體系的困難、學校不了解學校社會工作、以業務重疊為由拒絕等因素考量之下,服務方案暫告段落,學校社會工作的發展轉而沉寂,沉寂時期的學校社會工作與民間試辦期大不相同,此時期的學校社會工作以社區資源的型態進駐校園,因此更加覺察學校社會工作的服務不應僅止於個案服務上,而是把角色延伸至各面向的整合(蘇培茹,2009),雖然如此,社會工作能否在校園中發揮功能仍取決於學校的開放程度。
歷經民間試辦以及沉寂時期之後,校園中的問題依然不減,1995 年兒童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通過,明定中途學校應設置社會工作人員,加上當時爆發數起少年事件,中輟生的議題因此廣被討論與重視,1997 年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民間機構試辦「將中輟生找回校園」的服務方案,雖連結警政、社政、衛政等相關單位,但仍各司其職,無實質上的合作機制,需要社工人員當中穿梭往返。1998 年2 月善牧基金會開始試辦「多元性向發展班」,同年8 月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合作,開始以「合作式中途班」的方式在中心內運作。2001 年,善牧基金會正式將「多元性向發展班」獨立成一個專為中輟生服務的單位「臺北善牧學園」。至此,校園外的社福團體積極的在校外著眼於中輟生的輔導,突顯校園中現有的輔導機制無法妥適照顧中輟學生,需要社會工作資源的介入,但是社會工作人員也僅是協助追蹤已經中輟在校外的學生,一旦學生要返回校園,主要決定者仍落入學校相關人員,社會工作者仍只是在校園的圍牆外協助,在教育體系中仍沒有適切的位置,惡水仍在,但惡水上的大橋尚未建造。
中央政府終於於1997 年推出「國民中學試辦專業輔導人員方案」,於臺北市、高雄市以及臺灣省執行,兩年後評估報告雖傾向支持續辦,但礙於教育部的經費因素停辦,並宣布由各縣市政府自行辦理,臺北縣、臺北市以及新竹市於1999 年陸續開辦。同時期,教育部也頒定「建立輔導學生新體制-教學、訓導、輔導三合一整合實施方案」,揭示由全體教師結合社會工作等專業人員,建立初級、二級、三級預防輔導體制(黃韻如,2009),如今,校園中依然依循三級的輔導機制進行。
綜合言之,我國學校社會工作自倡議至今,歷經多次變革,學校社會工作人員進入了一個教育專業主導的工作場域中,開始摸索教育與社會工作之間的合作模式,從制度的建構到困境的突破,透過各模式的實施與評估,終究希望可以朝學校社會工作的目標邁進,以發揮學校社會工作的專業成效。然而,學校社會工作者帶著自身的專業訓練、信念以及視野進入教育體系,與教育體系如何合作發揮效益仍是一條待開發的路徑。
本文將從校園現場出發,呈現學校社工在這歷程中的努力,明白一個以教育為主的校園,學校社工是如何在多元且複雜的洪水中架起連結教育和社政橋梁。並且試圖藉目前校園的輔導工作現況及教育現場學校社工的服務成效與困境,期望可以站在教育現場的位置進一步探究成效及困境引申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