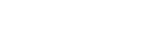第136期 健康照護與社會工作(2011年12月)
醫療社會工作績效評量與管理
臺灣醫療社會工作的發展,相較於深受其專業思潮影響的美國晚了45年,而1949年省立臺北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前身)社會服務部的成立,可謂正式開啟了臺灣醫療福利服務史的濫觴。由於社會工作在醫療領域中的推展,係以病患及其家屬社會心理層面之關懷為核心任務,此種運用系統性知識、方法、技巧,從生理、心理、社會、靈性等多元角度瞭解案主需求,進而完成專業評估、執行處遇計畫,以協助面臨疾病壓力之個人、家庭緩解生活危機的服務,不但可以呼應1930年代以來身心醫學界一再強調的「人為生理、心理、社會三者一體(as a bio-psycho-social entity)」的身心統合觀念,亦可以實踐世界衛生組織於1946年所倡議的「健康」理念(生理無恙與心理、社會層面的安適狀態),以及醫療全人化照顧(holistic care)的精神意涵。
然而,社會工作者初入醫療體系之時,曾因專業功能不被認同而遭致團隊中其他成員,尤其是醫師質疑與反彈的歷史經驗,則中美皆然。1970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院(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初設社會服務部門時,就曾遭醫師強烈抵制而禁止社工員進入病房(Bracht, 1978: 12),研究也指出:醫師和社工人員兩者之間對於個人罹病需求認定的角度不同,且就彼此合作必要性之評價亦存有歧見,雙方因此難以協同共事(Wilson & Setturlund, 1986: 8)。多數醫師只期待社工人員從事福利金申請及處理病患久占床位、疏導出院等「角色替代性」較高的具體服務(concrete service) (Wilson & Setturlund, 1986: 8; Smith, 1973: 443; 蘇秋莉,1977: 154;金蔚如,1988: 128;卓春英,1986: 114),故未予福利服務者應有的尊重。事實上,社會工作者在以醫師為主體的醫療專業體系中,原本即為從屬和配合者的角色已早有論述可循。首先,依照醫療社會工作者功能發揮的角度而言:「僅是配合醫師作業,從事預防、治療和傷殘復健等措施,運用社會工作專業方法來協助病人解決其有關的社會心理問題,以提高醫療效果」(姚卓英,1990: 691);其次,「對醫療範圍內的事務,醫師有絕對的發言權和判斷權。他們在科學和個人經驗間,扮演著啟承轉合的關鍵角色,使用科學知識的抽象語言以解釋個人的不適症狀…;對大部分人而言,醫師是接觸不可及領域的唯一媒介,所提供的乃是權威性的諮詢,在醫療照護的位階結構中,自主性與地位均超越其他人員」(Starr, 1982; 張苙雲, 2005: 215-216)。
由此可知,其後數十年,國內醫療社會工作部門逐漸增置,社會工作員員額也隨之成長的原因,與專業成效之間並無直接的關聯性,換言之,社會工作部門得以擴充,並非基於專業功勳受到肯定。根據王婉芬(1994: 60)的研究:社會服務部門在醫院組織中的設置和發展,是一種制度性接受(institutionally accepted)的過程,亦即當醫療文化認定「全人化的醫療照顧」為應然推動與實然執行的照護模式之時,設立社會工作部門則為醫院組織對此一制度性要求的必要回應。於是,省立醫院普設社會服務部(1967年),醫院社會工作者結合個體組成「中華民國醫務社會服務協會」(1983年)(1989年大會通過更名為「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而為了促使社會工作部門在醫院組織結構下,受到更多體制性的保障,透過該協會極力推動,行政院衛生署公布將社會工作納入醫院評鑑項目(1985年),正式認定社會工作者為醫療組織中不可缺少的一員。其後數年,衛生署更頒布了「綜合及專科醫院未滿100床者,應指定專業人員負責社會服務工作;100床以上者,每100床應有一位社會工作人員負責社會服務工作」之醫院評鑑專業人力配置標準,此外,亦範定了社工人員的專業任用資格,以及推展個案與團體工作所需的空間設施(1989年)。
儘管如此,在2003年修訂評鑑指標(降低「結構面」配分,增加「過程面」及「結果面」品質指標,強調「可近性」、「完整性」、「參與性」、「適切性」與「持續性」五方面執行成效的評量),以及2004年推動新制醫院評鑑之前,衛生署對「醫務社會服務工作業務」之相關評鑑項目內容,僅有「醫務社會工作」(配分5分)及「醫療品質保證--醫療關係的促進」(配分2分)兩項,而其中對於評量等級的內涵標準並不明確,由於配分比例相較於醫護主體顯然低微,因此,部分醫院並未在意社會工作專業在評鑑中的表現,當然,這也代表了社工人員在醫療體系中的專業地位、功能績效有待提升的窘境與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