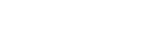第157期 國際公約與臺灣社會福利發展(2017年03月)
家庭與政府協力合作模式:以臺中市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運用團隊決策模式為例
近年臺灣社會關注兒童及少年虐待事件,政府重新體認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除社會工作人力增補外,服務模式建構亦刻不容緩。結構化決策模式(Structure Decision Making Model,簡稱SDM)之中安全評估量表(Safe Assessment Scales)引入,並且歷經本土化實證,藉此建立標準評估,避免實務社會工作者對於家外安置(Out of Home Care)評估太過與不及(劉淑瓊、楊佩榮,2011),而影響兒童及少年權益。因著安全計畫將保護因素與危險因素列入評估指標,照顧者、施虐者列入安全計畫並且成為安全評估的主體;換言之,家庭成員由過去被評估者、甚至是沉默者或者排除(Exclusion),轉變為傾聽者、參與者,甚至家庭成員的意見可以表達且成為安全計畫內容要項之一。因此,除了父母之外,家庭成員的參與與否,似乎成為一個關鍵,去觸發評估與決策重要因素。
國家介入父母親權並且參與兒童保護,已列入國際兒童權利公約範疇。兒童保護服務非將父母意見排除在外,反而應將家庭納入兒童保護決策考量,被視為更有利於兒童及促使家庭展現理性決策過程(Healy, K., Darlington, Y., & Yellowlees, J., 2012)。英國1988年推動「攜手合作」指導方針,即強調「從開始充分參與兒童保護過程所有階段」乃家庭成員的權利(Healy, K., Darlington, Y., & Yellowlees, J., 2012)。Healy, K., Darlington, Y., & Feeney, J. (2011)則認為雖然父母參與兒童保護決策可能充滿矛盾,惟父母參與決策或者意見表達,攸關公民參與決策的權利與理念,是當代不可或缺的普世價值,如同兒童最佳利益乃國際兒童權利公約核心般的同等被看重。
臺灣在推動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無法與父母、照顧者合作,經常是一線實務工作者最大困擾與痛苦(林萬億,2010;劉淑瓊及楊佩榮,2011),而國外許多關於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文獻也有相同發現,兒保社工在艱苦環境之下執行及擔負繁重職責(Hughes, 2010, Klease, 2008)。兒童及少年保護社會工作員確實承擔多重困境,例如維繫家庭角色、關係維持及確保孩子避免遭受傷害的法定職責等,而這往往相互衝突(Thomson & Thorpe, 2004; Klease, 2008)。因此,兒童及少年保護社會工作者雖然承受責難、抉擇與家庭對立與拉扯,但不可諱言,社會工作員仍然扮演兒童及少年保護的關鍵角色。
隨著O'leary, Tsui & Ruch,(2013)提出社會工作與個案間專業關係模型,強調社會工作與個案間專業關係是連接而不是分離,是鼓勵彼此相互聯結。過去Howe,(1998)建議社會工作者從了解他們個案開始,從連結開始到建立彼此合作的最佳實作(轉引O'leary, Tsui & Ruch, 2013)。因此,如何由個案連結至家庭,將家庭納入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運作,尤其家外安置(Out of Home Care)發生時,其所面臨衝突特別嚴重與艱困,家庭與政府之間彼此不信任,正如Chris Klease(2008)研究訪談六名孩子遭澳洲政府安置的母親,指出兒童及少年保護處遇干預程序復雜,難以被理解,家中的母親往往對兒少保護社會工作員充滿敵意和絕望,過程中母親感受遭受政府與兒少保護社會工作員的背叛、失信、指責與羞辱、失落及悲傷。Chris Klease但也指出最重要的一件事,兒童及少年保護體系對父母、家庭及利害關係人,能夠保持禮貌和尊重的對待,是開啟對談與合作的開始。因此本文探討家庭與政府在兒童及少年保護協力合作模式,並且藉由103年12月至104年12月期間執行98場團隊決策模式會議初步分析及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回饋,希冀能發展具本土文化脈絡的服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