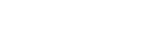第157期 國際公約與臺灣社會福利發展(2017年03月)
寫在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施行前夕——接軌國際實踐兒權,我國性剝削防制工作變遷中的保護意識
兒童性剝削被認定是一種性虐待(a form of sexual abuse)的形式(Pearce, 2014;廖美蓮,2016),也是一種性/別暴力[1]、一種權控(廖美蓮,2016)。性剝削經驗對兒童產生永久心理或生理上的傷害,且難以痊癒。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2](以下稱兒權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第34條清楚揭示各國應該保護兒童[3]避免受到任何形態的性剝削和性虐待(all forms of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sexual abuse),包括:兒童遭受性侵害、利用兒童賣淫、利用兒童色情表演及兒童色情等,均視為是對兒童的性剝削(廖美蓮,2015)。兒童性剝削(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CSE)[4]在臺灣已不是創新的社會議題(Cole et al., 2016;王曉丹,2015),政府各個體制-尤其是主管這個業務的社政與社福系統的各個層級-對兒童的理解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發生了許多變化,然而這些變化一直無法讓防制網絡的工作者懸置(bracketing)[5](Ely et al, 1990 cited in Liu, 2007)對涉入性產業的兒少存在質疑。性剝削的被害兒少始終無法被認定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稱兒少權法)中所指的性侵害保護個案是一樣的兒少,許多基層社工憂慮新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以下稱兒少條例)讓兒少與陪偵社工的專業關係更形拉扯;不少實務工作者也注意到多元處遇工作模式的法律規範在兒少保護資源嚴重不足的困境下仍處於茫然階段。
研究指出對兒少的性剝削行為將使未成年人產生「多重複雜的創傷」經驗(Graham & Wish, 1994),諸如創傷後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Farley et al., 1998; Tsutsumi et al., 2008)、損害兒少自我價值感、破壞其人際關係界線、對他人的不信任感(Curtis et al., 2008; Smith et al., 2009)、自殺念頭(Greene et al., 1999; Van Brunschot & Brannigan, 2002)、焦慮和沮喪(Tsutsumi et al., 2008)、物質成癮等(Nadon et al., 1998)(引自Cole et al., 2016)。為確保兒童受到保護及照顧其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需求得到滿足,修改法條,依據公約規範的精神,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的準則。同樣是兒少族群,性剝削相對於其他不同受虐類型的兒少,受到隱而未現的刻板價值與差別待遇,亦即兒少同樣都位在受到不當對待的困境,卻有不同的處遇;欲解決此一問題,應以國家制訂的法律與社會規範的形成並重,且彼此發展出合作關係。未來法律新典範;然而,朝向此一方向發展的困難似乎主要在於觀念上。如表1深色區塊的文字-「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查獲人數」的敘述方式也是一種社會真實的建構。這個類別的文字說明所指涉的兒少,究竟是保護性還是犯罪性?不僅語言本身弔詭,同樣是保護個案,一旦牽涉到性產業,就很難將「兒少主體」看成是一塊鐵板的整體。難道說兒少保護系統內的虐待類別也有再細分差序格局,如同表1明明都是統計兒童少年受虐人數與受虐類型,然而兒少性剝削的類型為何被排除在統計表之外?這些統計文本似乎也承載著政府管理者的眼光,意味著管理者對兒少保的想像與思維也許未能符合公約第2條「締約國應尊重本公約所揭櫫之權利,確保其管轄範圍內之每一兒童均享有此等權利…」。兒童權利委員會更呼籲締約國針對弱勢兒童提供特別協助,並透過積極手段協助該等兒童脫離弱勢處境(林沛君,2015)。因此,當社工被要求要將兒少性剝削視為保護個案之規格處理時,這個統計表卻又讓社工產生認知的斷裂與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