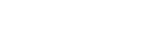第156期 保護性社會工作(2016年12月)
融入照顧創傷原則的親密關係暴力實務工作
親密關係關係暴力是人類創傷經驗的一種,人類遭遇創傷之後會產生許多不同程度的反應,Regehr and Bober(2005)指出,人類的創傷後壓力反應是一個連續體,從危機發生時的暫時功能受損à急性壓力症候群à創傷後症候群à到長期創傷後症候群,因嚴重程度以及持續時間長短,而有不同的名稱,但是都通稱為創傷後壓力反應,在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工作中,經常看到女性倖存者描述自己的反應,例如:長期失眠,經常做惡夢,有憂鬱症狀,想到相對人就害怕等,這些都是典型的遭遇親密關係暴力後的創傷反應,因此第一線協助親密關係暴力倖存者的社工員應該是需要介入處理創傷經驗的工作人員之一。
然而筆者多年來從事親密關係暴力相關研究而訪問社工員時,發現多數社工員只要在所協助的倖存者提到創傷的感受、反應與經驗時,立即想到將倖存者轉介心理諮商服務,將創傷感受/反應及經驗的處理,視為與其他的親密關係暴力服務分開的獨立服務。當筆者面對社工員異口同聲地反應在原本的工作流程中,就是這樣要求與設計時,內心不禁反問:人類創傷經驗影響如此之大,可以這麼分開處理嗎?倖存者在面對這麼多人生決定的過程中,例如:離婚、獨立生活、爭取監護權等,創傷的狀況不會影響這些過程嗎?在高風險家庭服務工作領域中,筆者也發現同樣的現象:在個案記錄表單中有一欄位是創傷處理,但是即使該欄位主責社工員勾選了,但是後續持續協助的社工員卻向倖存者建議轉介諮商輔導,將倖存者無法扮演適當母職的問題與倖存者的創傷反應分開處理,導致後續出現更為嚴重的保護性問題。只要是創傷議題就應該轉介諮商服務,不是社會工作應該處理的問題?
這個疑問在筆者的內心存在數年,臺灣社會工作領域中也一直未出現討論照顧倖存者的創傷反應的文獻,直到筆者有機會接觸到照顧創傷工作(trauma-informed care)的文獻時,終於有了清楚的看法:創傷的經驗會帶來一些症狀,思考混亂、情緒高張、解離等,如果治療的工作與情境未將倖存者的症狀加以考慮並且融入物理環境的安排、服務規範、服務範圍等,那麼將會引發或是加重倖存者的症狀,倖存者在協助/治療過程中有可能會採取拒絕、不合作等的態度(Savage, Quiros, Dodd & Bonavota, 2007);照顧創傷工作是一個範圍很廣的工作,傳統屬於心理諮商所進行的創傷治療是一個深度的,特定的照顧創傷(intensive trauma care; trauma-specific intervention),這種深度的照顧創傷經驗的目的在處理創傷症狀,但是必須和其他照顧工作結合,成為一個全面的照顧創傷工作,例如:和精神困擾處理、戒毒、關係問題處理等整合,從女性倖存者踏入家庭暴力防治機構開始,就開始照顧倖存者的創傷反應與需要,這才是照顧創傷工作的真正意義(Jennings, 2004; Mockus, Mars, Ovard, Maelis, Bjelajac, Grady, LaClair, Livingston, Slavin, Willams & McKinney, 2005)。照顧創傷工作模式強調從倖存者整體的環境思考創傷的處理方法,強調充權、促進安全、以及鼓勵倖存者自我決定的過程,是一個非常適合社工人員採用的創傷處理模式(Savage, et al., 2007)。
前述的定義清楚解答了筆者過去的疑問,因為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經驗是一種創傷經驗,因此當家庭暴力防治社工員第一次接觸到暴力倖存者時,就已經開始從事照顧創傷工作,接受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社工員協助的過程的任何一個步驟,都是照顧創傷的一環,不是只有心理諮商師所進行的心理諮商才是創傷經驗處理。除了照顧創傷工作的定義解答了筆者多年的疑惑之外,筆者同時也發現照顧創傷工作已經開始融入西方的家庭暴力實務工作之中,因為家庭暴力本身就是一個創傷的經驗,西方的家庭暴力領域的工作模式雖然極力的增強家庭暴力倖存者的權能(empowering),因為家庭暴力倖存者長期遭受暴力對待的關係,因此情緒或是精神狀態經常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如果社工員不關注/不處理倖存者的創傷情緒,在這樣的工作過程中經常再度讓倖存者受到創傷,因此西方的家庭暴力防治領域就積極加入這個視角(Andryczyk, 2015; Wilson, Fauci & Goodman, 2015)。家庭暴力領域引用照顧創傷模式是目前西方的趨勢,值得我們借鏡。
在臺灣,呂旭亞和詹美涓(民98年)從帶領女性遭遇親密關係暴力倖存者的團體失敗經驗中,指出數個失敗的可能原因,包括:女性倖存者與一般女性混合使用同一棟空間,讓女性倖存者覺得自卑與不自在,女性倖存者的時間與服務時間的配合程度不高等,因此造成團體失敗,所以建議協助女性倖存者的工作流程都必須加以調整。呂旭亞和詹美涓(民98年)的看法也同樣是照顧創傷工作的一環,支持了筆者對於臺灣親密關係暴力防治領域實務現況的觀察,亦即,臺灣親密關係暴力領域需要加入照顧創傷工作模式。
當筆者瞭解這樣的模式之後,引發筆者好奇,如何將照顧創傷工作加入現階段臺灣親密關係暴力社會工作領域之中?因此筆者就以此問題作為本文企圖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