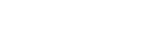第156期 保護性社會工作(2016年12月)
風險社會中的保護性工作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指出,2015年臺灣家庭暴力事件總數為116,742件。其中婚姻/離婚/同居關係暴力事件,每年案件數高達61,947件(占總數之53.06%)、兒少保護案件有21,360件(占18.3%)、直系血(姻)親卑親屬虐待尊親屬((孫)子女虐待父母、祖父母)案件有13,653件(占11.7%);另有其他四親等間的家暴事件約19,503件(占16.71%)(衛生福利部,2016)。
每到年終,臺灣各主要兒童福利團體,也總會針對重大兒少虐待事件提出檢討與呼籲-期待家長、社會、政府能有更積極的措施以保護兒童少年,使他們能平安、健康地長大。2010年的曹小妹跟隨母親自殺事件,排山倒海的責難輿論,重創了全國社工的熱情;也讓後續高風險家庭個案通報案量驟增;法定責任通報者,寧可誤報一百,也不可放過一個;結果是,各縣市高風險服務社工,光是第一次訪視篩案就快要做不完,很難往後顧及服務深度。爾後每年發生的重大兒虐事件,也總是一件比一件令人震驚。2015年,重大虐童事件標題分別是,「無良舅公虐童,一死一傷」(何小弟)、「狠母與男友虐殺嬰,燙熟分屍」、「17歲媽媽溺嬰棄屍,動物啃剩骨頭」、「憂鬱婦人攜二子女自殺」、「妒夫六刀殺妻,二子女目睹驚嚇」等,每一案件都令人悲傷。當年度共有68個兒少因受虐、家暴、或照顧疏忽等而死亡;且年齡有越來越小的趨勢。2016年3月28日,臺北市內湖區更發生隨機殺人事件,4歲的「小燈泡」不幸遇害,引起社會高度的憤怒、悲傷、和恐懼,要求政府必須儘速建立安全防護網絡,以確保兒少不再發生不幸。
類似「曹小妹」、「何小弟」的案件,在許多國家都出現過;英國的Victoria Climbié、Baby P,都曾引起社會譁然、媒體憤慨;美國每年有高達50至60萬件、至少1,500件致死的兒虐案件;而「社工臨床能力不足」是常見的調查結論。英國的兒童保護調查報告也曾強烈批評,社會服務部門,工作人員士氣低落、督導不足、個案負荷量高、資源不足與訓練不夠,所以出問題(Laming, 2003; 2009)。但是,事件過後,有多少問題真正地被解決了?抑或是,我們根本不該期待,這些現象,可以完全不再發生?因為我們處在一個無可迴避的風險社會之中?
為了回應這些家庭暴力悲劇,監察院近年來也積極介入調查政府福利與保護制度、兒少保護工作者的服務過程,是否有違失之處,這股究責文化(culture of blaming),加重了第一線保護工作者的恐慌與挫折。2013年,監察院通過監委沈美真、黃武次、趙榮耀提案,一口氣糾正了行政院、內政部、教育部,以及新北市等10個縣市政府。該糾正案明白指出,兒少保護社工人員評估判斷失誤、專業能力不足等問題。而地方政府之責在於,對社工人員職前及在職訓練情形及成效,沒有建立有效評估管理機制,任由社工在不具足夠專業能力情形下,承擔所有成敗及挫折。兒童及少年保護社工人力雖經內政部及各地方政府持續充實,但仍不足259人,不足比率達4成,導致社工人員處於高負荷及高壓力工作環境,異動頻繁,造成專業不足,無法久任,影響服務品質。此外,對行政院的究責則是,沒有善盡督導責任,導致中央機關規劃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家庭處遇,協調整合不足,各執本位(監察院,2013)。
2016年,監察院再次針對104年7月間媒體所報導的4起兒虐事件,包括新竹縣何姓小兄妹遭舅公虐待致1死、1重傷案、基隆市2歲林姓男童遭父親傷害致死案、新竹市1歲陳姓女童遭父親悶死案、桃園市9歲黃姓女童遭鄰居收留家庭持續虐待案等,進行調查。該調查報告指出,「兒少保護社工人員是兒少保護工作的第一線尖兵,代表政府對社會中的弱勢受虐兒少及家庭,提供妥善的保護與協助,但這些社工人員卻處於三高「高案量、高壓力、高危險」的惡劣工作環境中。」、「兒少保護社工人員不僅出現人才荒,也面臨三缺「缺督導、缺合作、缺資源」的工作窘境,加上在校養成教育及專業訓練過程又不足夠,使得第一線的年輕兒少保護社工人員在短短幾年之後,將社工職場的熱忱立即消耗殆盡,紛紛轉換職場,引發人力流動頻繁、專業經驗無法累積的惡性循環。」(監察院,2016)。
2016年3月,一位施姓男子,歷經撤銷羈押、另案服刑期滿被釋等司法程序,直奔新北市汐止區,槍殺了長期受到他高壓權控、施予精神與肢體虐待的妻子。這起案件於2013年間,曾三度被通報進入系統服務,但卻因社工前後以電話、家訪聯繫未果、警察登門訪查亦遭阻擋、推託,而未能真正與當事人見面,最終採信相對人的言詞而未積極介入。當槍殺案件發生後,監察院亦啟動調查,認為社工僅憑前後各一次的短暫通話,就認定被害人無意願或安全無虞而予以結案,是缺乏積極作為與缺乏敏感度的。
換言之,「社工專業知能不足」、「保護性社工人才荒」、「缺督導、缺合作、缺資源」等問題,已成為監察院報告一致性的結論。然而,社工為何專業知能不足?是專業教育過程、還是實務訓練上有所不足?甚麼樣的工作環境、服務模式、和技術文化,讓社工變成監委眼中,消極、缺乏敏感度、挫折的助人工作者?監察院報告雖然究責機關多於究責個人,但到了基層,離職的、懲處的、寫報告的、被放大檢視記錄的、悲傷自責的,還是基層社工。於是社工們上街、上網怒吼著:「不是社工殺人,是制度殺人!」、「我是社工,不是神…」!
誠然,不管是「權控妒夫殺害妻女」、「恐怖情人分手暴力」、「小爸媽親職失能」、「憂鬱父母攜子自殺」、「同居人性侵凌虐兒少」、還是親生父母對孩子的施暴與疏忽照顧,受害人大多都是相對資源薄弱、自我保護能力不足的婦女、兒少、老人和身障者,因此亟需政府以公權力介入保護,亟需社工以敏銳、積極的熱誠,提供專業的服務,這是保護性社會工作的使命。然而,我們也要問,每年超過十萬的家庭暴力保護案件,究竟誰可以承擔如此之重的期待?本文認為,保護性社會工作渴望達到「安全」和「穩定」,正好與「風險」、「混亂」對面而立,「控制風險」也成為服務對象和助人者最重要的任務,風險管理的技術應運而生。風險管理的知識和技術運用,也已然從科技、經濟領域,滲入到政府治理系統。在此潮流下,風險管理影響、也改變了社會工作的樣貌。
用一支牙籤,凸著一顆西瓜?
首先,讓我們先借用Ulrich Beck「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的概念,來理解當前保護性社會工作面臨的環境。風險社會的概念指認,人類在現代化社會中,面對產業、藥品、汙染、核能、天然災害等意外事件,會產生各種焦慮與恐懼;Beck認為,不論是風險事件本身或是人類的焦慮,都已非專家或制度,就有足夠的能力去克服。但因人類仍然必須每日面對這些現代性風險的副產品,因此,人們總是努力想要預測風險、控制風險、消滅風險。而為了應付這些難以預測的風險,人類不斷發展更精打細算、更專業的科技,來處理風險事件,最終衍伸出「風險管理」這門知識(許雅惠、張英陣,2016)。
保護性社會工作,可謂是日日與風險為伍,活在惶惶不安之中;故而會發展出一種以「恐懼」為核心,努力尋找克服恐懼的方法和策略,確保風險控制的工作文化。此一風險管理導向的社會工作發展,在歐美已經非常成熟:在控制風險的期待下,人們傾向相信,只要透過客觀和科學的方法,找出指標、計算機率、制訂風險評估工具;最終我們可以用特定的條件累積、指標總和或組合等數據,推論預估風險模型,達到預防、控制風險的目的(Houston & Griffiths, 2000)。因此,許多保護性社會工作,為了能降低不確定性的焦慮感、清楚地掌握風險,便不斷地發展各類評估風險的工具、各種能快速篩檢個案危機的方法,以求能精準地判斷服務對象所處的風險程度。
近幾年來,臺灣的保護性社會工作,確實也以「檢測風險」為主要的發展目標,一套一套來自歐美國家的風險評估工具被借用、改造成本土的測量工具。這些工具被普遍認為,有助於幫助第一線社會工作者,作出當下、緊急階段的實務研判和決策。然而,保護性社會工作絕不能僅限於此。風險檢測之後,我們必須追問,各種配套措施是否到位?合理的個案量是否達標?後續的服務資源是否可得?助人者敏銳的情境察覺能力應如何培養?是否有充份的教育訓練和督導支持?本文作者常以「一根牙籤,凸著一顆西瓜」,來形容保護性社會工作者的微小與無奈。他們手裡掌握的太少,卻被要求承擔的太多!
風險控管的概念一但進入治理程序,似乎變成一根無所不能的金箍棒。政府、民眾、媒體、民意代表,彷彿認為有了標準化的評估工具,個案死亡或重傷事件就不會、不應發生;認為如果意外與危機一再地發生,就代表社會工作失靈、是無效的專業(Webb, 2006)?試想,幾項題目、一張紙,一個加總分數,可以代表甚麼?代表我們可以依照分數高低,決定開案或不開案服務?代表我們可以依照分數高低,決定多久去家訪或電訪一次?當風險控管概念延伸到服務程序時,是否只要按照法定規則和程序來執行,就能確保風險消失?當然,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在人與人的世界裡,認知、感覺、情緒、行為,無一不是瞬息萬變的動態過程-如何預測?如何控制?
理論與實務都告訴我們,親密關係中的受暴婦女,或許面臨到父權法律與家庭文化的壓迫,或面臨到經濟權力資源之不足,或是社會支持體系的疏離孤立,必須依賴男性的經濟供給與權力控制,以交換與子女相依的生存機會,所以她們會隱忍暴力,習得無助。但隨著年輕世代的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經濟自主性增強、性別平權意識充份,長期的受暴隱忍樣態逐漸減少,親密關係暴力的重大致死案件也明顯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親密關係雙方互控彼此為施暴相對人、男性受暴比例上升、卑親屬虐待尊親屬、其他四親等案件之通報量逐年增加。這也意味著,親密關係暴力雖然仍占高比例的家暴案件,但只要我們提高了被害人的「保護因子」,「危險因子」自然也會下降。
另一方面,不管是成人暴力的相對人,還是兒少的施虐者,總能看到他們與長期失業、罹患精神疾病、藥物酒精成癮、有犯罪紀錄、賭博惡習、情緒控制與人格違常等危險因子如影隨形。檢視諸多個案,會忍心虐待、傷害無辜兒少者,不是因為吸毒、精神疾病、失業、酗酒而喪失正常心性;就是因為經濟壓力、缺乏社會支持而走上自殺絕路。而逐年上升的卑親屬虐待直系尊親屬,那些殺父弒母的,也多是因為欠債、藥酒癮、失業、精神異常,要錢不成、溝通不良、所犯下的悲劇。這些風險固然可視之為個人的不良德性,但更多可被歸咎於社會生態的崩壞。這些充斥在結構環境中的社會風險,往往都超過個人所能負荷、因應。
增加保護因子,等於降低危險因子。所有家暴事件的遠因與近因,鑲嵌在一個多層次、多因子的問題結鍊之中;而問題之解決,則取決於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之消長。家庭身處的失業、中輟、犯罪、社會網絡、藥酒癮、精神疾病、身心障礙等問題,解決的機制為何?強化保護因子的社會資源和社會連結在哪裡?保護性社會工作者,擁有那些技藝和資源,可以對抗諸如失業、精神疾病、毒品、犯罪、疏離、個人主義、貧富差距等諸多罪惡?
本文認為,風險評估與測量工具,多半著重於了解風險的表徵,並未能深入關注服務對象的需求。但若因此將社工的服務引導至表面問題的解決,久之則會讓實務工作者,喪失整體脈絡評估的敏感度。更甚者,如果社工只重視風險判斷、強調降低風險程度,卻忘了背後造成風險之結構性問題,如貧窮、失業等,才是真正的敵人;則社會工作的價值將大打折扣。以一支細如牙籤的個人力量,試圖對抗結構環境的壓迫,恐怕是令人易折與早夭的。
制度性的風險與防禦式的決策
如同監察院報告所指,在新管理主義下,講究效率、競爭、組織精簡的大纛下,地方政府僅以「購買式服務」方式,委託民間團體承辦各項兒少高風險家庭處遇服務,但卻未能提供合理的經費,致無法吸引專業資深社工人員留任與投入。但真正決定預算編列、人力核給、資源建置等決策者,恐怕不是只有業務主管機關而已。兒少保護的三級預防體系,因政策發展脈絡不同而被切割分段管理,從經費、組織到直接服務,經常上演著你加碼我減價、你丟案我不撿的爭議戲碼;整個保護體系在統整性與連貫性上,的確有所不足。
兒少保護越來越往三級處遇的路上走,雖是一種不得已;但也是一種長期輕忽保護因子的結果:我們是否應更加強前端的一級預防?同樣地,成人保護個案,雖也發展危險分級評估,但整體通報案量的暴增,使得人力即便增加,社工還是疲於奔命。垂直整合、相對人處遇服務、多元處遇、目睹兒少、一站式、預防性認知教育等等,不斷衍生出來的方案,看似大量的人力與資源投入,但真正改變的是甚麼?目前的成保被害人實務工作重點,仍多侷限於初期的人身安全議題討論,甚少能延伸到後續的生活重建或認知教育;是否能說我們已經增強了保護因子?
社會工作服務,本該兼具預防、發展與治療的功能;但風險社會的來臨,讓社會工作逐漸走向事後救急、治療性處遇、風險管控之途。由於風險來得又快又急,預防工作已經成為一種侈言。近年來,社福資源與社工人力多增加於保護性工作,大量的資源投入家暴、兒保,初級預防面臨邊緣化,連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等二級預防經費,也逐年遞減(許雅惠、張英陣,2016)。為了規避風險,安置兒少可能成為社工處遇決策的最安全、簡便的管道,但安置後呢?寄養家庭、機構管理、家庭處遇計畫,工作的取向如何?家長是否改變?兒少可以回家重聚的比例有多高?
在越來越不確定的環境中,為了確保社會工作能為服務對象降低風險,所採取的技術往往是更多的管制化、標準化的作業程序與工作流程。為了風險管理,在實務過程中更加地強調社工應遵守規則與程序,所以社工成為「依法行政」者,實務工作變得越來越「例行化」與「麥當勞化」,社工面對電腦,開會、準備評鑑的時間,是否比面對個案更多?
Beddoe(2010)認為,社會工作如此重視風險評估,是一種害怕產生錯誤的恐懼反應,而非提供更好的處遇;而社工的角色也愈來愈少在作「正確的決策」,而只是在「捍衛決策」。當臨床社工不再對自己的專業判斷有信心,他們只好藉由以風險評估表來決定開案與否,也以風險評估所得之分數等級,來決定服務期程與服務頻率,像是一個月該有幾次電訪、幾次面訪,成為一種公式。
在一個充滿「究責文化」的社會中,社會工作實務將會變得防衛性越來越強(Parton, 1996)。組織為了降低風險,將許多重要的風險辨識與控制任務,外包給外部專家,似乎要把自己的決策交由外部專家確認之後才能安心。例如,普遍出現於保護性工作中的「結案評估會議」、「高危機網絡會議」,更是期待藉由外聘一些未直接接觸個案的專家,在短短的時間內聽取社工服務報告,然後作出要不要結案的建議;安全防護網高危機個案(馬瑞克)會議、兒少保與高風險個案均需進行解列、結案評估會議等。結案評估會議之召開,是否代表社工員與督導的專業判斷不再被信任?甚至社工們自己也不再有信心,而希望另聘一位「外部專家」來給予建議,期能降低「出事」的風險?這種做法只是讓社工更退縮、更防衛、更怯志;更有愧於專業二字。
所以,本文呼籲,監察院應停止對重大保護性案件,進行不必要的質詢與監督,因為問題的癥結發生在暴力的更前端,經濟、就業、貧富差距、犯罪、成癮、疾病,誰也脫不了干係。如果政府治理都無能解決這些問題,就不應該苛責保護性社會工作,因為這是治理失能,而非專業失能;社工不應成為風險社會下的代罪羔羊。
不確定性中,更需要反身性思考
風險社會中存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其中又以保護性工作最感壓力。兒少保護、家庭暴力、老人照顧、身心障礙、精神社會工作、觀護工作等風險性高的實務環境,被要求以更具效率的督導與風險管理(Parton, 1998)。但若社工服務過於仰賴風險評估工具與標準化作業流程,則會導致評估、反思能力之喪失,讓實務工作變成一種機械化的被動回應;社工服務也會因缺乏思考,而失去了社會工作的彈性與敏感度。越是恐懼風險、越是需要控制;社會工作領域出現越來越多的績效評鑑、細如牛毛的評估指標、越來越多的照表操作、越來越多的記錄與文書登錄。當整個組織、督導、社工都忙著依照各種績效指標做事時,個案的福祉是否真正地被關照到?
以證據為基礎的實務,是否過於讚揚客觀性的評估,而貶抑了主觀性的評估?以助人專業來說,專業者本身的知識、經驗、人格特質、直覺等,是否重要?如僅透過標準化工具,加總計分以推估風險機率與程度等,是否足以作為決策的依據(Gillingham, 2006; Stanford, 2011; Stokes & Schmidt, 2012)?一再地抑制、監管風險,是否將形成對社工專業深度的侵蝕?甚至讓社工淪為一個依法行政、按表操課的技術官僚?更強烈的批判則認為,只專注於對抗風險的保護性工作,將使得社工忘卻以個案權益為優先,遠離社工專業的精神與價值;因為風險保護的主角將不再是個案,而是組織、制度、名聲及工作者。
本文並非否定風險評估的重要性,也認為發展標準化風險評估工具,的確可以避免實務工作者因經驗不足、知識缺乏、錯誤判斷、遺漏等原因,未能及時辨別「風險」的「風險」,協助社工實施後續之「以證據為基礎」的處遇服務(Gillingham, 2006)。風險評估甚至可以成為提供法庭裁決的證據、具有決定資源分配的優先性、降低服務提供者的風險等功能。特別是在究責文化高漲的壓力下,行政程序與評估文件,如程序記錄、評估表等工具,將成為「服務系統」的保護傘。當社工確如中央規定,在一定期限內,每天早、中、晚分時打電話卻聯繫未果、如實登打記錄、風險評估分數也未及危險、符合結案指標,的確就是可以結案;即便個案發生危險,也能明確指出誰或制度該為此負責(Green, 2007)。
過去的社工,因為需要在專業發展中摸索與匍匐前進,因此反而有了更寬廣的空間,可以進行反身性學習。但是當前的社工,在風險社會下臣服於管理權威,受到更多管理者的控制,甚至由管理者決定績效目標,逐漸喪失了反身性思考能力,對專業認同與價值造成相當大的威脅。失去了洞察力與實務主體性的社工,也失去了承諾與熱情。這是當前臺灣保護性社工人力大量流失的原因,也是資源投入再多,也填補不了的空洞。
風險社會中的社會工作發展變得相當弔詭:在不確定性中原該更重視專業判斷的,但現實卻是變得更依賴標準程序,用以風險管理。當社工員面對服務對象與自身風險的不確定性,為了躲避堂而皇之的究責文化,保護性社工被迫必須採取「防禦性」的決策和機械化的被動回應。在企業界的生產過程中,標準化作業過程確實有助於降低風險的傷害;可是在助人專業中,面對人與環境的複雜性,標準化作業與客觀的風險評估雖然具有引導作用,卻不足以處理多變的實務情境。要面對複雜且多變的社會工作實務,更需要社工員不斷學習新知,不斷的從實務情境中反思自己的處遇經驗,運用專業判斷作風險管理(許雅惠、張英陣,2016)。
Donald A. Schön(1983)認為,社會工作關係是處在複雜、支離破碎、不斷轉變的世界中,所以要掌握「不確定」原則。他主張的「在行動中反思」(reflection-in-action)就是要將理論融入實務中,社工員要在實務中反思,要在實作中思考。在行動中運用知識,就是將理念與行動不斷實驗的過程,將知識轉換到不同的實務情境,並進一步檢視其有效性。風險社會中的社工需要更勇敢,更積極主動的反思能力,而不是更多的控制工具。期待本文,能引發更多關注社會工作實務的反思與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