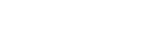第138期 當代社區工作(2012年06月)
從跨國經驗看臺灣長期照顧政策中的照顧權
臺灣自1993年進入高齡化社會後,對於長期照顧需求的迫切已經被政府以及許多的學者重視(吳淑瓊,1998;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6;行政院,2007;林萬憶,2006),政府部門對於人口老化所衍生的健康、照顧、經濟負擔等問題,開始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計畫,包括1998年推動「老人長期照護三年計畫」、1998~2007年推動「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2001~2003年由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推動「建構長期照護體系先導計畫」,2004年成立「長期照顧制度規劃小組」,2007年行政院又核定了「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旗艦計畫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詹火生,2009)。而2008年政黨輪替後,規劃的方向又轉向了以長照保險的方式來處理,形成了臺灣對於長期照顧一直沒有明確的政策定見現象。檢討臺灣有高度長期照顧需求的原因,不外乎看到人口快速老化、失能人口急速成長、少子化造成人口結構改變等因素,同時也認為婦女的勞動參與增加、家庭功能的改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8;王雲東,2009;紀金山、劉承憲,2009)。這樣的發展與其他OECD國家的變遷趨勢沒有太大的差異(OECD, 2011),然而臺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雖然自1989年的45.4%提升到2009年的49.6%,但相較於挪威在2007年達到69.5%、美國在2008年達到59.5%、即便鄰近的韓國在2008年亦達到50%,可見臺灣的婦女參與率並不算高(行政院主計處,2010)。另一方面,從行政院主計處(2010)的分析也可以看到,臺灣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雖然逐漸提高,惟就不同的婚姻狀況針對性別的差異來進行觀察時,就可以發現兩性在未婚時的勞參率差異不到1個百分點,但一進入婚姻,差距即刻拉大,兩性的差距可以達到24.6個百分點,顯示婚姻左右了女性勞動參與的意願。由此可見,以「家庭功能式微」、「婦女勞動參與率提高」做為長期照顧需求增加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即說明了長期以來臺灣將「照顧」視為是家庭的責任,而且也是婦女的責任,勢必影響臺灣在規劃長期照顧政策時的思維。
不同的學者對於「照顧」有不同的定義,它可能包括了每日在生活、心理、情緒及生理上的照顧(Knijn & Kremer, 1997;Karisson, Mayhew, Plumb, & Rickayzen, 2004);不同的國家對於「照顧」的提供也有不同的政策,比方說Esping-Andersen (1999)區分出家庭主義(familialistic)和去家庭主義(de-familializing)兩個福利體制,而更多的學者為了進行福利國家間的比較分析,發展出許多具性別敏感度(gender-sensitive)的新概念(Kroger, 2011),代表了不同國家對於「照顧」的價值理念非常不同。然而,本質上對小孩、失能老人、障礙者或病人的照顧,並沒有所謂有償或無償的區分,「照顧」成為有償或無償的議題,是政治選擇的過程,是文化信仰和性別結構的結果(Knijn & Kremer, 1997)。國內外對於「長期照顧」的議題有非常多的討論,例如關於醫療的利用(Deraas, Berntsen, Hasvold, & Forde, 2011)、服務的提供與使用(張文典、楊雯如、莊文玲、黎秉東,2011;羅玉岱、林沛嫻、張春瑤、江怡慧,2011;施麗紅,2010;邱啟潤、黃鈺琦,2010;蔡啟源,2009;Damiani, Farelli, Anselmi, Sicuro, Solipaca, Burgio, Iezzi, & Ricciardi, 2011)、家庭的角色(Zhan, Feng, Chen, & Feng, 2011)、制度的檢討(黃源協、吳書昀、陳正益,2011;陳正芬,2011;Mendelzweig, Bedin, & Chappuis, 2011;de Blok, Luijkx, Meijboom, & Schols, 2011)或照顧設備的改善(謝嫣娉,2010;林金立,2010)等,惟較少討論「長期照顧」的權利問題及責任歸屬,尤其臺灣的長期照顧政策常停留在如何支持家庭提升照顧能力。比方說政府的長照十年計畫基本目標即在「支持家庭照顧能力,分擔家庭照顧責任」(行政院,2007),以及如何透過私人購買來獲得照顧的提供,例如藉由外籍看護工的協助來滿足照顧的需求,而此項措施利用人數遠遠超過政府所提供的居家服務人數(184,602:30,207)(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1;內政部統計處,2011)。
「長期照顧」的議題特別值得關注,除了有迫切的需求外,也涉及到性別的問題及權利的問題。因為多數的國家都是由家中的女性來負擔照顧的責任,而且多數是無酬的工作,這不但影響到婦女的健康情形,也影響到參與勞動市場的機會、工作的選擇及貧窮的風險(OECD, 2011)。然而事實上,「照顧」應該是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當環境有需要時,有權利主張應該立即獲得適當的照顧,這個權利不應該有性別的區分。而「照顧」做為一個公民權利的概念,更應該包含同時擁有照顧他們關心的人的權利,以及在必要時接受他人照顧的權利,只有當照顧變成公民權中的必要面向,給予照顧、被照顧和公民權才能去性別化(degendered)(Knijn & Kremer, 1997)。
探討照顧的「權利」問題,Knijn & Kremer (1997)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架構,他將照顧的概念分成「給予照顧時間的權利(The right to time for care)」以及「接受照顧的權利(The right to receive care)」兩個概念,前者係指在特定的時間上,照顧重要他人及自己的權利,涵蓋了正式照顧及非正式的照顧,一個典型的例子即是在勞動市場中提供照顧假或允許彈性工時,這讓公民可以在提供照顧的同時,持續參與勞動市場,也讓照顧不被視為是一種道德要求,阻擾了公民自主選擇不提供照顧的權利;而後者指的是依賴機構能提供各式不同品質的照顧服務,當國家所提供的照顧服務擁有好的品質,且讓公民可負擔,所有的公民才能夠享有受照顧的權利。而要瞭解臺灣對於長期照顧的政策作為,以及從不同國家的長期照顧經驗來進行跨國分析,Leitner (2003)針對家庭主義在老人照顧政策上的差異所進行的國家理想類型(idea types)分類,提供了一個很好選擇該採用哪些國家的經驗來進行分析的一個分類基礎。依據Leitner (2003)的區分方式,家庭主義依據照顧政策的差異可以被分類成四種家庭主義類型,包括了選擇的家庭主義(optionally familialistic)、明確的家庭主義(explicitly familialistic)、隱含的家庭主義(implicitly familialistic)以及去家庭主義(de-familializing),惟Leitner (2003)所認為的去家庭主義在老人照顧政策上並沒有歸類出足以代表的國家,因此實際上僅區分出三種不同的家庭主義型態,代表的國家之一分別是瑞典、英國和荷蘭。由於本文的重點並不在探討長期照顧服務提供的方式或制度應如何規劃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而是採用Knijn & Kremer所提出的兩種照顧權利概念,來比較不同國家政策對於長期照顧的支持程度,同時藉由Leitner所選取出代表老人照顧政策的三種家庭主義模型的國家,瑞典、英國和荷蘭,做為跨國比較的代表國,再納入臺灣的長期照顧政策一同進行比較,以凸顯臺灣的長期照顧政策是否有從「照顧權」的概念來回應長期照顧的需求,以提供未來政策決策者無論是規劃「長期照顧保險」、「長期照顧服務法」、亦或「家事服務法」,能有一個不一樣的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