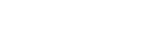第110期 高齡化社會福利政策(2005年06月)
論全球化與本土化交會下的新社區
社區是個人成長與生活的處所,不論其時間、空間到地域皆為個體建構自我與群我認同的依據,不過,在資訊科技與溝通媒介多元化與高速化的趨勢下,社區不單是個人與生活世界建構關連性的一環;也是個體實踐與全球接觸及親近的場域;有人以絕然的目光審視此現象,認為個體已經喪失對自身文化與風俗的認同感,只是任憑挾著資本主義聲勢而來的商品和消費所淹沒;可是,時勢所趨,在另一旁熾熱地燃燒著卻是廣受宣揚的「本土化(localization)」。
臺灣80 年代社會科學界倡言「本土化」的呼聲極高(李亦園,1985;楊國樞、文崇一:1985;蔡勇美、蕭新煌,1986),而這樣的反省延續迄今(李永展,1999;蔡培村,2001;蕭全政,2000),而且範圍更廣,並落實到生活、教育、環境等層面,反省角度也從最初努力提出適合這塊土地之風俗民情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檢討整個社會知識背後隱藏的預設和意識理路(葉啟政,1987:2〜3);進而從歷史和政治經驗上去探討本土化所受到的限制和應該突破的範疇(陳昭瑛,1995:6〜7)。
學術界一方面致力於為自身研究對象、方法論及理論基礎探索本土化的內涵;一方面也無法漠視全球化所牽動的諸種衝擊和社會變遷。對社區來說,身歷全球化與本土化兩股浪潮,追求共榮共存的開放性應該勝過優勝劣敗的單一性。到底存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是何種可能性?全球化淹沒了本土化?本土化驅趕了全球化?還是兩者交雜出混沌不分的大熔爐呢?會不會有一天人類的區分指標變成「全球化人類」與「非全球化人類」?就算這樣都還不是最糟的,如果兩者形同陌路或敵意相向,那才是屬於人類的悲劇(陳淑敏,2001:143)。
社會化歷程裡,當個體離開家庭之後,在積極參與社會、國家的過程中,往往會經過社區的洗禮,本文在於表明全球化和本土化乍看之下,似乎背道而馳,但無可諱言的,生活並不會因為經驗全球化而失去本土認同的需求(無論具象或情感);也不會因為本土化就可以自外於全球化趨勢的籠罩,而臺灣本土化更不是政治意圖與權力鬥爭,更非刻意挑起族群敏感神經的工具(中國時報,2001.5.12,13版);當然,臺灣全球化的實踐,也不單只是參與國際體系、環境生態、民主人權、網際網路等不斷向外延伸的方向,關於向內延伸至社區生活、文化深耕、主體建構等立基於日常生活世界的議題,亦無可迴避。
臺灣整體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1]隨著各種組織與國際架構的參與,更加納入所謂「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運作邏輯裡,「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做為社區文化研究者,本文試圖從理論層面探索全球化或本土化對社區的意義及其可能性為何?以釐清社區、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的關連性並對此議題建構系統性的思考;為當前社區的發展提供新的內涵、思維,據為實踐的指引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