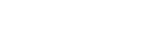第117期 國際潮流與社會福利(2007年08月)
國際社會福利趨勢:潮流與務實
隨著英國首相Tony Blair的下台,1990年代盛極一時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思潮似乎也面臨如何持續下去的窘境。這是潮流的宿命,有漲潮就會有退潮的時候。
在上一世紀的七十年代,John K. Galbraith就提醒渴望救贖的世人流行思潮的不確定性,他說:「……用上個世紀已成定論的經濟思想,和本世紀眾說紛紜尚未成定論的思想作對照,上個世紀資本家們都肯定資本主義的可行性,同樣的道理,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者也都一廂情願地肯定他們的信念終會得到最後的成功,至今這些言之鑿鑿的信念卻很少能經得起時代的考驗……。」同樣地,在21世紀的今天,也有著太多的流行思潮。
除了「第三條路」取向之外,1990年代其實是個福利思潮百家爭鳴的時代,這些色彩鮮明的福利觀伴隨著1980年代末以降蓬勃發展的社會運動而興起,它們對社會福利的分析有其特殊的切入角度,進而自成一套看法,雖然或許沒有「第三條路」取向般綜融,不過由於立場的簡單明確,其訴求也就單刀直入而具備相當程度的洞察力。它們的觀點有些的確受到「第三條路」取向的吸納,但不宜將之歸屬為同類,如此反而喪失其作為一個特殊福利觀所擁有的價值。
底下我們不妨簡要檢視一下這些爭鳴之中的福利觀。首先,以性別為切入點,女性主義(feminism)掌握了社會結構中男、女兩性間的不平等,以及因之而來的所謂「性別盲」的福利政策,尤其著重於批判父權主義式的與以男性家庭生計者為核心的傳統福利體系。不論是透過要求女性在教育、就業與社會地位上享有平等的機會(即自由主義式的女性主義論者)、要求女性不要被視為男性的附庸而享有完整的社會安全給付與普及的公共兒童照顧方案(即社會主義式的女性主義論者)、或是強調女性的獨特性而要求為女性量身定做各種服務與措施(即激進的女性主義論者),她們都主張女性也是核心的社會經濟構成要素,而應享有與男性一般的同等對待。所以任何「社會福利」絕不能立基在以女性作為犧牲品的假設上,例如認為撫育兒童為女性的天職(所以男性可以上酒吧而不必待在家裡)、或貶抑婦女為無酬的家庭勞務工作者(所以不能像有正式工作的男性般享有完整的社會安全保障),如此的「社會福利」只不過是「男性福利」的藉口而已。
第二,以人與環境生態之間的關係為切入點,綠色主義(Greenism)企圖建立現代社會的環境生態倫理,隨著其立場強烈程度的不同,又可分為「淺綠」與「深綠」兩大分支。「淺綠」基本上接受現今的世界秩序,也認同經濟穩定成長與消費的重要性,它所要求的只是對環境的友善性,強調「永續經營」觀念必須深植於經濟的成長與消費之中;而「深綠」的立場則較強烈,它認為現代科技並無法解決目前環境生態的問題,除非我們的觀念有了澈底的轉變,也就是放棄不斷的經濟成長與消費,而人類也只是地球上億萬種生物之一,人與萬物是平等的,而不是高高在上或擁有萬物的生殺大權。當這樣的理念轉化應用到社會福利領域時,綠色主義強調普世的平等觀,反對過度強調科層體系與消費的福利國家形式,尤其是伴隨這類福利體系而來的科層(專家)控制與剝削,國際間的貧富差距應該消除,但不是透過永無止境的經濟成長,而是讓人類需求與生態資源更密切契合的永續發展。
第三,種族主義(racism)以一個社會裡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為切入點,彰顯出社會裡少數民族的處境,往往沈淪在社會結構與生產關係中的最底層,也使得種族問題與階級問題糾纏在一起,成為被剝削的對象;尤有甚者,在強勢文化的宰制與洗禮之下,少數民族也逐漸喪失了其傳統的生活方式、文化、信仰與價值,他們不僅是經濟上的少數與弱勢,也是文化上的少數與弱勢。因此,種族主義論者主張提供必要的社會服務(尤其是在教育、訓練與健康方面)給少數民族,但這樣的提供並不是立基在「補償」、「施捨」、或只是「吸納」與「同化」,而是立基在社會整體再分配的哲學上,擴展最大的社會福祉,而且這些服務措施必須具備文化的敏感度,尊重少數民族的生活型態,也貼近他們的真正需求。
第四,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捉住了社會分工與生產方式的轉變作為切入點,從過去緊密分工、總體經濟管理、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社會經濟型態(也就是福特主義),轉變到強調彈性的分工體系、彈性的生產過程、彈性的勞動力、乃至強調研究發展能力的社會經濟型態(也就是後福特主義)。簡單來說,亦即從強調大眾一致的需求,轉變為強調小眾多樣而彈性的需求。隨著這樣的社會分工與生產方式的轉變,過去強調穩定供需關係的凱恩斯式福利國家也必須有所調整,它必須鼓勵勞動力的更新與創新來提昇國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社會政策因而要配合勞動市場彈性化的需要,這不僅只是工作生涯與福利給付之間的結合而已,更是多方面地讓勞動力可以自由往返流動於家庭、社區、學校、乃至職場之間,協助人的潛能充分發揮,而不是將之固著在退化中的單一領域。
與後福特主義常共同出現的則是後現代(postmodernity),它以現代社會生活型態與倫理價值的對照作為切入點,有部分學者將後現代與後福特主義連結在一起,不過前者更著重在倫理價值面的變化。工業革命後的現代階段,社會生活強調的是普遍性的價值與一致性,尤其是對物質力量的崇拜,結果人的本質與自我容易被窄化為工具性的存在,而喪失了其原本擁有的創造性、浪漫性、與美的欣賞。相對於現代階段,後現代階段裡的人們更在意自我個性與幸福的追求,他們不再單單仰賴或滿足於住宅、健康、就業之類的物質安全,而更關心於生活的品質,所以物質性的再分配不再是議題的全部了,人們更期待解除一切對人的本質的壓迫形式,包括父權主義、結構的不平等、乃至過度強調工作與成長的經濟型態。然而,在追求自我的過程中,不確定感與危機會油然而生,同時著重個人差異也與平等的理念之間存在著相當程度的緊張關係,這些正巧是集體式的福利國家亟思克服的部分,所以個人與集體之間的矛盾在後現代社會中尤其強烈。對此,後現代的處方是一個更開放的溝通環境,形塑成人們之間的彼此信任與公共制度的責信(accountability),也就是不論人們對彼此之間的需求、或公共制度對人們呼聲的回應,都應是立即而無障礙的,才能有效降低個人與集體的公共制度之間的隔閡與矛盾。
全球化(globalization)觀點的分析角度也是當今顯學之一,以資本主義經濟的全球性脈動與民族國家權力之間的關係作為切入點。一個新的世界經濟已經逐漸成形了,而它也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籓籬,透過大量跨疆界的貨物與服務的交換、國際間的資本流動、以及科技迅速而廣泛的擴散,世界各國在經濟面上已被緊密的互賴結合在一起。全球化的脈動是超越國家疆界的,也因此對傳統之民族國家的權力產生了衝擊,除了改變自己以因應這樣子的發展趨勢之外,各國並無法透過個別的國家政策來修正、控制、或改變這樣的發展趨勢;其次,如同Mishra所強調的,一個經濟浪潮不但不會舉昇起所有的船,它可能還會打翻擊沈許多的船,沒有一個國家會期待自己是被擊沈的船,因而更加激化了國際之間的經濟競爭;最後,這樣的趨勢會對福利國家產生不利的影響,一方面它仍然侷限在民族國家的傳統疆域之內、另一方面消費性的福利給付可能會耗損國家的國際經濟競爭力。也就是在這種思考底下,Giddens乃亟思以「社會投資國家」取代「福利國家」,將消費性的福利支出導向具投資意涵的社會領域。
除了英國Giddens的「第三條路」取向之外,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也以James Midgley為首提出了「社會發展」(social development)取向,雖然其影響力似乎較侷限在美國西岸、加拿大與部分環太平洋的地區(尤其以香港與中國大陸討論較多)。如同1980年代盛行的新右派思潮一般,社會發展取向也是以福利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為切入點,但大異於新右派的是,它強調這兩者之間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互為根本,而且是個有計劃的社會變遷過程。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確保經濟發展以改善人類的福祉,所以經濟應維持適度而均衡的成長,但這是以整體發展作為主要的著眼點,而不是藉由犧牲某一部分以獲得最快速成長的扭曲式發展;同時,我們也必須透過社會福利來促進經濟發展,因此必須更著重於有利於人力資本(如教育與訓練)、社會資本(包括物質面的基礎建設如交通與衛生、與社會面的基礎建設如社區和公民社會的互助支持網絡)、以及促進就業或自行創業的措施。
而在歐陸,社會品質取向(social quality)是晚近崛起於歐盟(European Union)的概念,在荷蘭政府與學界的支持下,結合其他國家的學者成立一個基金會,推動社會品質概念的建構,做為指引歐洲社會模式的發展方向。我們知道在歐盟走向整合的過程之中,如何維繫各國既有的生活水準,成為民眾是否認同歐盟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以絕對的角度來說,這意味著生活水準即使無法提昇、至少也不能降低;而以相對的角度來說,這意味著歐盟不能放任各國現存的生活水準差異任意擴大,否則相對剝奪感的產生會損及歐盟整合的可能性。為了促進社會面最大的整合,歐盟已發展出「排除╱包容」(exclusion/inclusion)的政策取向,而社會品質取向則是進一步地擴大,納入了經濟安全、社會包容、社會團結(或凝聚)、與自主性(或充權empowerment)等4個指標,做為衡量各國生活水準的依據,同時也是各國社會政策必須戮力追求的目標。
在新福利思潮不斷冒出頭來的過程中,諸多老的、但卻具重要意義的觀念也重新受到檢視,甚至被賦予了新的生命,社會凝聚(social solidarity)是其中之一。「凝聚」(又譯為「連帶」或「團結」)是法國社會學家Emile Durkheim百年前所倡導的重要概念,用以指涉一個社會秩序建構起來的方式,已經從過去強調同質性的機械凝聚轉變為強調異質性但卻互補的有機凝聚。而這也就構成了法國福利國家的核心,亦即立基在互助與危險分攤上所建立起來的凝聚感,將整個社會結合成一個互為保險的社會。但由於經濟活動的日益分化,我們發現某些經濟領域的人們較其他人有著更高的風險;復因政治決策過程未能準確掌握這個變化對社會凝聚的負面影響,致使大家逐漸失去對國家福利的信心,社會秩序的根基因而受到了侵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更積極地思考與重新界定各種社會方案,某種程度上的選擇性(selectivity)是必要的,但它並不必然意味著具烙印效果、嚴苛的資產調查,或許將這種選擇性的基礎置於較客觀的或生理性的因素上,如身心障礙、年老、夕陽產業的勞工……之類,較能重新建構出適應新時代變化的凝聚感。
另一個則是生命歷程取向(life-course),早在1901年,Seebohm Rowntree即已提出貧窮的生命循環理論,說明人的一生中在兒童期(年幼沒有謀生能力)、中年初期(子女還在依賴階段而食指浩繁)、與老年期(體力衰退生產力下降)最容易掉入貧窮的困境。今日這個理論再度受到重視,並進一步發展成「生命歷程取向」的福利觀,希望建構出因應不同生命階段所面臨之問題的社會方案,使得政策與生命歷程之間的關係有更緊密之結合。因此在兒童與青年階段時,政策的重點應在教育與訓練,提供青少年人口生涯發展的基本能力;在就業階段則著重於提供機會與安全,讓青壯人口能夠奮鬥與衝刺,這不是只為了此時的他自己而已,也為了他老年生活的需要預作準備、更為了有效提供其子女成長所需的資源;到了退休後的老年階段則著重穩定與保障,維持其生活水準。而在每個階段中,危機管理是必要的支持機制,讓危機能夠分攤,不僅是在其生命歷程之中、也是在人際或跨世代之間。
在這麼多紛紜的福利理念當中,並不是任選一種即能付諸實現的!社會福利的發展會受到制度因素的影響,亦即是理念上的「可能」並不代表現實上的「可行」。Esping-Andersen的體制觀點也是這類論點的典型代表,他發現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社會民主三種福利體制,在所面對的問題、能夠擁有的政策選擇、乃至政策因應所產生的結果三方面,都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所以當我們研究一個長期的社會福利發展時,過去制度因素的影響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這也就是學界所強調的「路徑依賴」論。
路徑依賴論認為一旦某種制度的發展啟動了,就很難再任意逆轉,其原因有二:一則,社會制度具有自我增強的作用,會逐漸改變了特殊環境下的行動者;二則,這些行動者會有其政策偏好,而這又與他們所處的環境息息相關。我們不妨用白話一點來解釋,當一個福利制度建立起來之後,它會產生一批與它有密切關係的人們,不論是這個福利制度的受益者、行政官僚與專家人員、或是這個制度成本的主要負擔者,他們會依照這個新的社會關係而組織起來;而當這個制度要被捨棄或改變時,這些已習慣於舊制度的人可能會抗拒這樣的轉變,不論是因為既得利益或對未來新制度的不確定感;就算是大家都順服地接受了新的制度,由於剛開始時的不熟悉或制度設計上的缺陷,可能也會產生運作上的不順暢、挫折與衝突等問題;這些問題又會進一步促成了下一個階段的制度改革,但對已經接受這個制度的人而言,類似的抗拒又會再產生。
於是,制度的改革就只能在漸進的基礎上,這並不是否認激烈革命變遷的可能性,但其所耗費的成本與失敗的風險,相對地要高了很多。這是決策者與高舉新風潮大旗的英雄們應當嚴肅面對的課題。或許有人不相信這樣的看法,讓我們來回顧底下這兩段話:
「許多複雜的社會問題中,現在沒有比失業問題更難解決的。這個失業問題不但在賣勞力的勞動階級感著痛苦,在賣腦力的智識階級的失業者之慘狀,實比勞動階級為尤甚……其應急的對策,一方面要積極的興起救濟事業,以開就職之路去調節勞動力的需給關係,另一方面要消極的講究對於就職不能者如老幼、廢疾、狂人……等的救護法,以保障其生存權。」
「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下,商工業愈發達的地方,貧窮的人愈多……社會上的貧者越貧、而富者更富……然則台灣政府對於貧富兩階級在怎樣處置呢?……在台灣所實現的社會政策,完全是主從的、差等的、喜捨的狀態。」
直覺地,你會以為這是現代學者或報紙對近年來台灣失業率升高所產生之問題及其對策的評論,但事實上第一段文字卻是出現在昭和4年(西元1929年)8月4日的《台灣民報》第272號社論,那時的台灣還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但所面對的社會問題、以及輿論所提出來的對策,卻與今日幾乎沒有兩樣。雖然時空條件變化極巨,新的福利理念、政策與措施趕流行般地不斷出現、並被引入到台灣的福利實施之中,但古老的幽靈卻從未消失,我們所努力對抗的、或是所追求的,與七十餘年前我們的前輩並無太大差異!
而所引述的第2段話則是出自昭和2年(西元1927年)1月30日的《台灣民報》,一位署名菊仙的人批判日本總督府的社會政策。在這一段強烈批判的話語之中,直指台灣社會福利的父權式本質,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下,國家的福利措施充其量只是溫和地潤滑資本主義的運作罷了,既談不上修正資本主義、更遑論社會主義革命了。冉冉73年的光陰過去了,社會福利似乎仍未脫悲情,依舊掙扎於資本主義國家之下,這究竟是歷史的弔詭?抑或是社會福利的宿命?而身處於當代的我們又是否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到什麼樣的教訓呢?
因此,在世紀交替之間百家爭鳴的福利觀中,我們的核心問題不應是「我們要選那一個?」,這樣的問題無寧是過度輕忽了台灣過去數十年來社會福利發展所形成之制度因素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也過度割裂了這些福利觀與其所處之環境脈絡的關係。我們的核心問題應該放在:我們究竟從這麼多觀點之中獲得什麼洞見?而這個洞見又如何與台灣的政經發展脈絡結合在一起,進而構成完整的施政風格?如此,才能避開「炒短線」或「缺乏治國理念」之譏,也才能合乎長久以來建立本土社會福利體系的呼聲。
這是一個不確定的年代,因為太多紛紜、但卻也都言之成理的觀點充斥在我們的周遭,雖然這些觀點多仍有待時代的檢證來證明它們不但是理念上的「可能性」,也具備了現實上的「可行性」。然而,如果我們無法對自身的問題與能力加以清楚地掌握與理解的話,那麼這個不確定的年代可能會更加沈淪為「迷惘的年代」,設若如此,我們不禁要為台灣未來的福利發展感到擔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