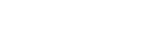第116期 國民年金(2007年05月)
國民年金制度發展的三道挑戰
自內政部於民國82年4月首度組成「國民年金制度研議小組」以來,我國政府歷年對國民年金政策議題多次但未決的公共討論,迄今正在向第15個年頭邁進。依照最近95年7月底「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的決議共識,國民年金法應在96年完成立法。不僅民間社福團體對此有著高度的期待,行政院團隊也開始加快腳步。而在前政務委員林萬億主導之下,行政院版國民年金法草案已經於本(96)年4月12日送行政院審查,行政院審查通過後於同年5月3日送立法院審議。
再次面對這一重要時刻,我們仍可以預見前面有著三道重大的挑戰迎來。第一道挑戰當然是要如何走出長久以來擺盪在政治化與經濟化的兩難洞窟。第二道挑戰則是如何跨越國際組織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間,右派(私有化)/左派(公共化)意識型態對峙的議題認知洞窟。至於在第三道挑戰中,我們還要能回應社會整體變遷與個人/家庭生命歷程轉變,所突顯出來的靜態時間歷史意識洞窟。洞窟總會讓我們執著於既有的知識、利益、權力、價值和規範,而走出一個洞窟卻也不能總是保證我們已經脫離了偏執獨斷的危險陰影,特別是對那些愛好使用簡單而有力、「非此即彼」二分法戰術的倡導者和論戰者。面對著這些多重並糾纏交錯的挑戰,21世紀的老年經濟安全制度安排,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傳統的資產調查救助、公民津貼、繳費保險和強制儲蓄等的時代功能與制度意義,最根本是與國家未來各世代人口整體社會福利發展的關聯。
國民年金的政治反覆或社會前進:走出政治化與經濟化的兩難洞窟
隨著行政院的加快動作,朝野仍舊緊跟著表態要再次提高老農津貼和相關給付規定,而無視於經續會社會安全組所做成的一項重要附帶決議:「開辦前中央政府不得再加碼現有各相關津貼或新增津貼項目」。經過團隊審慎的考量後,行政院對此項要求的回應,傾向不跟隨起舞,何況這項決議當時也曾獲得行政院的承諾。然而這些隨著即將來臨的年底立法委員選舉和明年總統大選,這種由稅收支出的「老人津貼」和繳費制的國民年金保險制度間的衝突性競爭,將再次成為台灣民主政治成熟度和公民治理的關鍵考驗。
十多年來國民年金政策議題的官方討論和演變過程,卻顯示出另一種「政治問題經濟化」的反制策略。受到西方一九八○年代新右派的福利改革潮流影響,特別是倡導一種「高度市場化(私有化)」烏托邦(或譯「烏有之鄉」)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有鑑於民主大眾選舉所帶來的選票競爭,以及造成國家財政赤字和累升債務,他們反向地主張和要求政府不應該干預經濟事務,更重要的是,他們還不斷地強調,要能避免「福利亡國」的政策。
這種對治藥方的基本想法,是認為人們只想要用選票來解決貧窮、失業和社會不平等問題,絕對是行不通的。就先不要談教父級思想家海耶克(Frederic Hayek, 1899~1992)指責20世紀人類所幻想的「重分配(社會)正義」──不僅在知識論上是不可能的,也因此在倫理學上同樣是不可欲的問題;至少現實上,多數重分配政策的努力,經常是造成更多的特權和既得利益團體,甚至是貧窮問題的不斷持續,和可能更為不平等的逆向重分配。所以學者們也常在實證評估研究中,發現各種的「中產階級得利」說,或「不是為了窮人」說。
然而面對各種新興社會問題、貧窮人口日益擴大和不平等程度的急速惡化,這種傳統上主張「消極自由」的新古典經濟學,也被迫逐步地轉向更為威權、積極地家長主義式(Paternalistic)的「強迫個人自由」:無論是以公共權力來強制個人「勞動」(工作福利,workfare),或是強制「儲蓄(含公積金)」(或以誘導手段「輔導」累積資產, asset-based),或其它能讓個人「不依賴」社會資源的必要手段,養成這類個人的基本「公民德性」(civic virtue),來支持個人行使其「自由」和「理性」的消費選擇能力。這一歷史性的理念大轉變和全球擴散,在我國國民年金討論過程的第2階段開始大幅地滲透(民國85年國家發展會議決議:「建立妥適之勞工退休金制度,增定國民年金、勞工老年附加年金採保險或公積金制度」),在第3階段則更躍升為主要的競爭政策選項之「一」。
反覆在「經濟問題政治化」對「政治問題經濟化」這兩種邏輯間,我國國民年金政策從第1階段(民國82年4月至84年5月)內政部起草,並由經建會接手擔任起整合角色,主導規劃和評估;再經歷第2階段(民國85年11月至民國88年9月)確定放棄全民健保式的大整合,而(路徑依賴地)採用無其他保障者另行單獨納保模式,又終因921重大災難暫告中止。隨後的二千年輪替,新執政黨啟動了第3階段(民國89年5月至94年1月)偏向「個人儲蓄帳戶制」的經濟主義修正,在民間社福團體強力反對之下,第4階段(民國94年2月至95年7月)才明確地回到社會保險路線,並再由內政部主導立法草案擬定工作。
在這一循環擺盪間,經濟邏輯和政治邏輯的交互錯置外,並經常忽略了社會邏輯的自主性,及其作為政治經濟制度的正當性構成基礎。其次,在人口家庭結構變遷、鬆動性別體制對兩性關係的重組,以及勞動市場的高度彈性、去標準化趨勢下,古典理解的社會邏輯,特別是以「男性養家模式」勞動階級家庭為社會團結(包括世代契約)的基石,也產生了巨幅的變動。職業結構和勞動模式轉變對勞動或社會團結的衝擊,一如家庭人口結構轉型的影響,特別是人口老化和少子女化造成的「領取者眾,繳費者寡」難題,都直間接地引發了對「社會保險模式的終結」之疑慮和憂心。或者說,就算擺脫了經濟邏輯和政治邏輯錯置的左右困境,我們還是需要對當代社會邏輯的歷史構成,有足夠充份和更新的理解來因應。
多層次的收入安全──尋找公共與私己責任的適當關聯
如果說,在20世紀末左、右意識型態衝突外,還是可以有種較為妥協和務實的有限共識基礎,那應該就是對收入安全的多層次制度安排,以強調個人、家庭、企業、政府間,如何適度分配各自責任、財務負擔和給付資格,以確保國民老年經濟生活,進而安定與增進家庭生活的品質。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全球性的福利改革風潮以來,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都致力於面對新的社會變遷情境,選擇在既能給予人民足夠保障,又能夠維持在財務承擔範圍之內的多層次制度安排。而這一妥協共識的基本精神,即是認識到沒有一種制度安排是完美,且可以單獨地擔負起新世紀的社會經濟需要。假定我們可以從德國一八八○年代的勞動老年給付保險立法(1889)和稍後丹麥(1891)的資產調查式老年年金算起,這種妥協共識的產生,事實上是經由各國百年來推行不同制度形式老年經濟生活安排得失中,所獲得的經驗產物。
如眾所知,一九八○年代福利國家財務危機跟隨著先前世界性經濟危機,暴露出其制度安排的脆弱本質,以及缺乏因應結構性變動的能力。主要民主工業發展國家的政治權力結構,也因此開始有了重大的變動,特別是自二次世界大戰後長久執政的社會民主傾向的政黨,也迫使各國政黨和勞資團體相競找尋新的制度理念與建構。對年金改革而言,其中較具代表性和建設性的,當然是國際勞工組織和世界銀行分別在1993年和1994年所先後提出的「多層次年金制度」。前者提出的,是一個以強制性的確定給付制為主的多層次年金架構,而後者提出的卻是一項以私營的、確定提撥制為主的多層次年金架構。這也顯示出兩者對於公共責任與私己責任間的適當關聯,以及如何增進人民福祉的安排,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伴隨著福利國家危機和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一九八○年代也正是國際勞工組織和世界銀行這兩個國際組織,個別影響力起伏的關鍵年代。在危機之前,國際勞工組織以社會保險作為制度典範,並透過國際公約和技術協助,推動戰後各國社會安全體系的建立。而福利國家的財務危機以及各國家庭人口結構的根本變遷,直接地威脅了社會保險典範的運作與永續能力。在這歷史背景下,國際勞工組織自我修正地提出一多層次的年金架構來做回應,包括承認並納入強制確定提撥制的層次,來增加個人私己責任的承擔部份。但除了其影響力顯然已經大不如前,這一(社會救助或稅收給付的最低給付──社會保險年金──強制確定提撥的儲蓄帳戶制──自願私營年金)四層架構基本上並無太大新意,特別是對主要工業開發國家現行年金體系的改革建議,沒有實質性的衝擊。
相對的,世界銀行的影響力是在一九七○年代開發中國家的債務高築和金融問題不斷地嚴重化,才開始成為影響各國財政和金融重建的重要機構。更重要的,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們也相信開發中國家儲蓄率高低和經濟成長的直接關聯,因此如何透過強制性確定提撥制的年金來提高儲蓄率,間接地帶動經濟成長,成為世界銀行介入年金體系改革的起始點。一九九○年代進一步透過人口老化的政策議題,他們將私營的但強制性確定提撥制,植入和替換成一個強調個人私己責任的多層次年金架構中,希望藉此可以在開發中國家產生高儲蓄率,同時穩定國家財政並帶動經濟成長。這個以稅收補充性救助──私營強制確定提撥和完全準備制──私營附加職業補充構成的三層年金體系,超過世界銀行提供開發中國家必要貸款和管理技術的能力,而產生並擁有了相當大的影響力。一九九○年代的拉丁美洲各國年金制度改革和稍後中東歐各國的年金制度改革,是主要工業國透過世界銀行來推動的。雖然世界銀行主要是以開發中國家為主要對象,但這種年金私有(營)化的政策構想,卻是以美國領導的新自由主義(或稱華盛頓──國際貨幣基金──華爾街共識)的產物,並與主要工業(已開發)國組成的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相互聯手推動。所以一些已開發工業國也在沒有世界銀行的介入下,推動了類似的私營強制性年金方案。在這世界潮流中,我們的近鄰香港,也在爭議近二十年後,於1995年強行建立的私營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南韓則是個特例,雖然在金融危機中受制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卻終究沒有採取這一選項。
在多層次年金架構的重新包裝下,國際勞工組織和世界銀行分別代表了社會民主模式和自由市場模式意識型態競爭的延續。國際勞工組織重申年金給付水準的可預期性和保證性才能確保老年的經濟生活,並譴責確定提撥制將年金給付的制度運作,完全暴露在通貨膨漲和不確定的投資報酬率中。除了不切實際地相信強制提撥即等於儲蓄率的提高,還假定儲蓄率的增加就會帶來國家的經濟成長。如果我們還記得,凱恩斯(Maynard Keynes, 1883~1946)早已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第一波全球化的歷史經驗中警告我們「自由放任的終結」:因為儲蓄太多和有效需求(購買力)不足,資本外流將惡化國內失業並昇高國際惡性競爭,資本主義因是轉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大規模世界爭戰。
相對的,世界銀行相信私營的強制提撥制可以經由儲蓄率的提高而促進經濟成長,並得以避免政治的不當扭曲。反過來,他們也批評國際勞工組織的架構,只會造成難以避免的政治任意操作和長期公共財務的赤字與虧損,甚至還是所得重分配的結構性惡化和勞動市場退休行為的不當扭曲。的確,以勞動人口為保障基礎的社會保險制度,除了長久以來為人詬病的性別和階級分配不平等,晚近世代分配的不平等問題亦逐漸受到關注。但是僅以消極、不介入的不作為方式,來減少重分配效果和免於積極政治操作產生的惡性逆分配,很難稱得上是真正的解決問題和進步。
有了這樣的認識後,我們應該知道多層次年金架構本身並非是個直接明確、沒有意識型態負擔的出路選擇,更不是個治病的萬靈丹。九○年代在工業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中同時進行的年金改革風潮,因此有相當多的修正或混合型式,特別是參考新加坡施行多年公積金的公營單一層次強制儲蓄模式,對於總的成效評估也未必有一致的看法。我國在國民年金規劃的過程中,也深受到這些國際思潮和爭論的影響,特別是由經建部門主導的規劃過程,確定提撥和強制儲蓄曾是被當做維持經濟成長的要素,也因此強制個人儲蓄制成為我國社會政策改革的重要選項之一。
依照多層次年金架構的理想設計來看,目前我國勞基法勞工退休金制度已經改制為公營的確定提撥個人儲蓄帳戶,而非世界銀行主張的私營模式,而且看來規劃中勞保給付年金化和單獨立法的國民年金,都會朝向社會保險模式的確定給付制。也因此看來會更接近國際勞工組織模式:社會救助──有最低年金給付(如津貼)的社會保險(勞保給付/國民年金)──公營的職業強制個人退休儲蓄帳戶──自願的商業私人年金或儲蓄。不過更為根本的挑戰,恐怕還是來自於社會保險邏輯本身順利運作所須要倚賴的社會結構條件的重大變化,不管叫它們後工業化、後現代化、全球化或是高齡社會。
社會保險、社會變遷與新的生命歷程政策與政治
相對於強制提撥儲蓄有難以真正確保個人老年生活的爭論,國民年金與公勞保分立和單獨立法的設計,則容易讓外界有「窮人相互取暖」之虞的問題。也是在這個問題之上,自第2階段規劃以來,就不斷地困擾著民間社福團體的支持意願,也使得立法過程更難以順利進行。的確,依賴大數法則來進行風險分攤管理的社會保險制度,其前提當然是要有足夠可以相互分擔和貢獻的人口群。讓原來就缺乏保障的人集合在一起分攤風險或進行重分配,當然是效果較不顯著。但不管是為了不讓原有軍公教、勞保的潛藏債務問題溢出,或是為使實施國民年金制度之阻力較小而維持軍公教、勞保體制,國民年金將只涵蓋一些未就業和繳費能力較弱之人口群,即使強行開辦,恐將面臨保費(最低年金設計也會造成繳費意願低落)徵收不易之困難,或者根本就只是回到現行各種老年福利津貼的原點。如果說當前我國需要保障的老年人口群都已經或多或少擁有最基本的津貼給付(約占80%)或其它職業附加給付,而未來需要保障的勞動人口群(25~65歲國民)也從原欲保障之384萬人逐步縮小為約353萬人,那開辦的急迫性(想藉此減輕老年津貼的財政負擔反正也不太可能)是否依然還存在,反成為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這仍可將進一步引導到採行「階段論」(與勞保年金化平行規劃、同步進行)或「一步到位」(如直接擴大勞保來納保辦理)的整合策略,以期化解國民年金分立架構設計對風險分攤管理機制運作的困難。
然而我們的問題並不只在於國民年金社會保險是否值不值得開辦的爭議,或是如何達到整合或融合的政治過程安排。我們這裡要關心的倒是更根本的挑戰:倚賴「足夠的」有繳費能力的勞動人口群,來進行大規模風險分攤管理和重分配的社會保險模式,是否還能夠在這個經歷大變動的世紀交接時代,繼續且有力的扮演好它的社會穩定功能?整體社會結構的轉型趨勢中,至少有社會的、經濟的和文化的這三種主要層面,透過對當代家庭生活周期模式和個人生命歷程模式的轉變,影響著這一問題的答案。
緊隨著人口老化而帶來對少子女化(未來勞動和繳費人口補充不足)的關注,成為工業國家討論「高齡社會」和家庭制度變遷的共同背景。未來勞動人口的減少和老年依賴人口的增加,當然是「直接地」衝擊了社會保險的運作邏輯。但經濟全球化對各國經濟發展和勞動市場結構的影響,特別是彈性化勞動(有酬工作的就業型態)和(勞動/資本)收入的兩極化(流行的「M型社會」說),卻「間接地」限制了社會保險的財務永續能力:一面讓擴大中的工作貧窮人口(working but poor)繳不起保費,而「理財有道」高利得的有錢一族也急著要去擺脫社會保險所帶來「不必要」(如美國發生的抗稅運動)的繳費負擔,或者矛盾的說是一種自願性的「社會排除」。至於正在塌陷中的「中產(或更無意義的稱為中間)階級」,則成為風險社會中「貧窮的民主(普及)化」的結構主體。最後,但較為不易「科學的」察覺,則是(後)現代文化生活的個體化消費主義價值全球擴散和(反動卻共生的)族群意識/地方部落主義的抬頭。在追求個人消費滿足或群體差異認同過程中,兩者都威脅著國家社群作為一個相互依賴和團結的生活整體,社會正義將成為「那曾是牢不可破但已煙消雲散」的歷史過往。
在20世紀初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困頓中,戰後出現了以「社會保險」為中心的社會福利「妥協共識」體制,透過標準化就業導向的生命歷程結構安排,朔造了出生教育到(性別分工下)成家/立業,而後到退休的人生三部曲時序模式,以及所謂的「男性養家/女性照顧」的典型(即使稱不上理想)核心家庭模式。一九七○和一九八○年代後工業化的服務產業經濟則開始打破了這一性別特定、標準化人生路徑的順利進行。在全球經濟競爭加劇的整合化和競逐最低成本過程中,產生了被視為是結構轉型陣痛的男性中長期失業、女性彈性(部份工時)就業和低度就業、持續家庭和兒童貧窮、婚姻不穩定和家庭解組等高風險或社會排除趨勢,並開始對生命歷程三階段間的區隔,以及所隱涵的生產性與照顧性工作間性別區隔產生了瓦解和去制度化的侵蝕力量。這些發展,不僅衝擊了我們對家庭和婚姻的想像與期待,也大幅地改變了生育(如少子女化對人口/勞動力結構的未來影響)、養育(如關注家庭暴力或外籍配偶問題)、托育(鼓勵婦女就業、增加收入)和教育(重視就業人力資本和勞動市場彈性化要求)間的連續性兒童政策,以及家庭中心的世代間相互資源倚賴和長期照顧安排模式。這些結構性的劇變,經由家庭、市場與國家領域中不斷發生的兩性和兩代間資源分配摩擦和權力/權利的爭奪,促成並侷限了個人生活計劃和生命歷程的彈性化選擇與高度不確定。
對於這樣的發展,很自然地會有三種相應的看法出現。一是樂觀地認為這只是邁向資訊經濟、網絡社會和未來更多個人自由選擇與自我創造的過渡階段。一是悲觀地感歎失落而要致力去重建舊有秩序和價值的安排。但要同時避開進步式樂觀主義和懷舊式悲觀主義,我們當然可以倡導一種較為自省的務實改革立場。這裡,工業社會男性養家/女性照顧家庭模式的式微,可以且必須被視為是一個來自現代性的矛盾和反思性重組的問題。男性養家(包括家庭薪資概念)模式所隱含的性別和自然宰制,本就內含有規範意義上的不可欲性。戰後的高就業率和經濟成長,無形中抵銷了(二次戰前就已存在)大半的反對和批判力量,因為現實的可行性,取代和正當化了缺乏規範可欲性的難題。當前在後工業新經濟與社會條件變化下,不僅帶動了男性高失業/女性彈性低薪等不穩定就業和貧窮的風險,進而雪上加霜地讓人們開始質疑這套模式在現實上的不可行。我們當前面對的挑戰,因是不在於如何去挽救和強化既有的家庭主義保障模式,而是去尋求如何與之脫鉤的新路徑。
同樣地,對於過度僅以「有酬工作」為就業典範和最有價值的社會活動,以致於成為貶抑照顧責任、家務工作、自願服務或社區公共參與為「非生產性工作」的「生產主義」(Productivitism),也在當前人口結構轉型過程中造成了「父母的反抗」(parent's revolt),和對「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或彈性安全(flexicurity)政策議題的熱烈討論。最後,對於如何超越「就業生活中心」的困境和探討「後生產主義」(post-productivist)社會的制度安排,所謂的福利津貼或「公民基本收入」(Basic Income)或參與收入(Participation Income),也伴隨著生命歷程對個人生命不同階段時間彈性使用的社會重分配,逐步地在歐盟成為重要政策議題,並擴散到美、加等國。在質疑社會保險是否還有可能的「後福利國家」年代中,後生產主義和參與/基本收入政策成為人們形塑個人新的「去標準化」生命歷程和開創新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新理想藍圖,來做為跳出進步式樂觀主義和懷舊式悲觀主義間無益循環對抗的另一可選擇出路。至於打開這個可能性的先決條件,則端視我們能否走出靜態時間的歷史意識洞窟。
國民年金制度的政策選擇與政治前瞻
讓我們稍加回顧一下先前所提到國民年金制發展所面臨的三道挑戰。第一道擺盪在政治化與經濟化兩難的洞窟,自是當前最受矚目的挑戰和關切的政治選擇議題。在這裡,如果國民年金制度的建立是這個政策的目標本身,則立法的成敗與否,當然就是最直接的指標。但如果國民年金制度本身並不是最終目標,而是達成保障老年生活和全體國民不論年齡的共同福祉,那麼當前立法的成功與否,就可以有不同的評價方式。對於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我們除了支持國民年金制度要去涵蓋全體國民老年經濟生活的理想外,我們也當要支持,甚至更要鼓勵去嚴肅地思考國民年金制度在未來20年或50年的任務和社會整體意義。在社會貧窮擴大和不平等加深的新世紀中,致力於保障老年經濟生活的國民年金制度也並非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道德難題,例如說「債留子孫」。在台灣兒童貧窮和基本生存也成為主要的社會問題時,如何協調世代之間的利益分配衝突,恐怕也不能不給予高度的重視,否則只會帶來世代衝突加深的社會崩解問題。
至於目前已潛伏成「非議題」的第二道意識型態對峙的挑戰,跨越「右派──強制儲蓄──私有化」/「左派──社會保險──公共化」的議題認知洞窟,並不全然就已經被克服或放棄。就在我們要去思考世代重分配的不平等問題時,不可避免的「個人責任的生命歷程自我重分配」就會重新成為一個重要的選項:強制個人自我勞動儲蓄以備晚年退休生活,差別大概只剩下到底該選公營的,還是私營的「家長主義」(Paternalism)。一種澈底的個人主義將在此架構下建制化,以消極、不作為地擺脫世代間或階級(或其它社會區隔)之間重分配的可能爭議。「社會保險的終結」就可能成為一九八○年代以來「去社會化」的實現,且可能會導致社會集體反抗的悲慘代價,一如19世紀資本主義擴張史的啟示。
最後,在行政院負責社會福利團隊的積極努力下,第三道有關社會整體變遷與家庭人口結構轉變的影響,包括高齡化、少子女化和移民等影響人口結構的問題和因應政策(人口政策白皮書),已經緊鑼密鼓地委託重要的學術研究機構辦理。但人口家庭結構變遷所帶來和反映出個人生命歷程多樣化問題,仍然處在一種「隱議題」的狀態,泰半方向多是以提供調整和平衡人口年齡結構方式的介入,而較少更為全面性的去思考「後生產主義」社會超越可能性或可欲性問題。雖然這仍不曾被當作是個迫切需要思考和檢討的重要問題,但對於任何試圖認真思考跨越「就業為基礎的社會保險模式」,這會是個機會和適當的起點。